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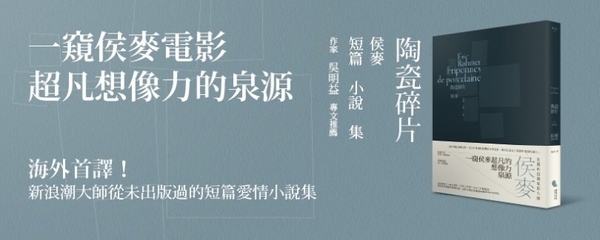
推薦序
微不足道的細節,如斯存在的人生(文/吳明益﹍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作家)
我要所有的男人都愛我,特別是那些我不愛的。
法國新小說與新浪潮
多年以來關於文學作品改編電影始終是影迷興味盎然的辯論題目,電影取材自文學作品當然沒有問題,但經驗已經告訴我們,並不是所有文學作品都適合改編成 電影;至少,並不是所有的文學作品都容易改編成電影。傑出的小說敘事者能把人物內在心理以細膩、準確、獨特的筆觸表達,而且他們的文字能讓讀者「徘徊再 三」,容許回頭在頁間躑躅。然而在電影院裡觀賞電影是無法回頭的,這使得兩者的閱讀基準大不相同,也考驗著導演的創造能力。
文學社會學家艾斯卡皮(R. Escarpit)曾說,文學改編成電影是一種「創造性的背叛」,不過在我看來,新浪潮時期的文學與電影的結合卻並非如此,至少侯麥將自己的小說改拍成電影並非如此。
多數評論者認為,影史上的「法國新浪潮」並沒有一個強烈中心主義,具有獨占性的美學形式與藝術立場的宣示,而比較像是一群氣質、風格各異的戰後新生代 導演,一次鬆散卻影響深遠的短暫集結。新浪潮導演共同創造了一個時代現象──他們在街頭或鄉村拍片,起用新的或非職業演員,自己寫劇本去探討想探討的主 題。
掀起新浪潮的年輕導演許多都出身於法國重要電影期刊《電影筆記》(Cahiers Du Cinéma),包括高達(Jean-Luc Godard)、楚浮(François Truffaut)、希維特(Jacques Rivette),以及較晚發跡的侯麥(Éric Rohmer)等等。
當時還有一批居住在塞納河左岸的「左岸派」導演(有些左岸派的導演不願被歸為「新浪潮」),最知名的當是亞倫?雷奈(Alain Resnai)。他與法國文學史上極重要的「新小說作家」創造了幾部經典電影:包括了和莒哈絲合作的《廣島之戀》,和凱羅爾(Jean Cayrol)合作的《穆里哀》,以及與霍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合作的《去年在馬倫巴》。
我還記得自己第一次看《去年在馬倫巴》時被那種迷離、複沓,如夢似真的敘事迷惑過、傷害的情形(覺得自己可能不具有觀影天賦),那樣的文學與電影的結 合並非是「創造性的背叛」而已,這部由霍格里耶撰寫分鏡的電影,反而造就了另一種文學──對敘事的探索冒險、彌漫在空間中的詩意,以及對接受者意識的挑 戰。
而在「電影筆記」的導演裡,則有一些導演本身就寫作,最特別的莫過於侯麥。他電影裡那些連綿不斷充滿機鋒、呈現出多角戀愛關係的對白,根本就是他年輕時所寫的小說的重現。
沒有故事的故事
侯麥曾在《六個道德故事》(Six contes moraux)的「前言」裡提出了一個讓人驚訝的問句:「倘若能夠以字句描寫一個故事,又何將它拍為電影呢?如果要拍為電影,又何必以字句去描寫它呢?」 影迷們或許會覺得侯麥已在電影事業上獲得聲名,這類的疑惑並不存在才對,但侯麥卻說這個問題實實在在地困惑著他。
侯麥是一位散發著文學性格的導演,他不像其他導演樂於穿梭電影節享受光環,據說在片場時也總是安安靜靜地坐在一角思考,嚴肅、嚴謹且低調。他說同樣的 故事由不同的人敘述,有可能出現差異(甚至完全不一樣),因此藉著對白與影像,侯麥的目的不只是揭露主角內心的想法,更是要「表明角色的觀點」。
經過了很久的時間,我才理解到侯麥的電影語言的特色,或許就是要觀眾隨著不同角色的觀點去思考──因為某個角色講出來的故事,很可能都是他(她)自己捏造的也不一定。(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捏造了什麼。)
以這本侯麥最初小說中那篇〈一天〉來說,滿懷妒意的男子賈克在知道情敵與情人見面後,搭訕了一位少女,並且在與情人對話中有意無意地提出來。「搭訕」 是他原本的說詞,但當情人提出質疑說為什麼他剛剛沒提這件事時(讀者可以感受到她的言語中表現出妒意),男子馬上改口說,「說是搭訕,也不完全是。我幾乎 是被逼的。」
這種曖昧感回頭瓦解了故事本身,言語無可保證,記憶無可保證,生命也無可保證。故事的「無目的性」,誘使讀者去思考角色情境,也設想自己如果陷入同樣 情境時的反應或者追求。讀者也會以自身的遭遇,去推斷這些人物的意圖。也就是評論者帕斯卡?博尼澤(Pascal Bonitzer)所說的「沒有故事的故事」(No story’s stories)。
在這本小說集的導讀裡提到,一九六二年初,侯麥接受《北方溝通》(Nord-Communications)雜誌的訪問時說,他把自己其中一系列電影 命名為「道德故事」,為的是以一種比較友善,不那麼嚴苛的方式,去探索內在生命裡、靈魂中某些不為人知的內心世界。做為導演,他「盡可能地以最謹慎的態度 在自己的內心迷宮世界裡摸索移動,前進,從來不去質疑什麼『大的議題』。」這裡的「道德」並非一般中文裡我們認知的做為行為約束社會共識的那種「道德」, 而像是影評人黃建業提過的,指的恐怕是那種「熱衷於描述人性內在的人」。這樣的人物往往苦苦陳辭,因而讓「語言囚禁了行動,意識形態遮蓋了現實,知性成了 欺瞞,邏輯申論夾纏虛妄。」(見《侯麥?四季的故事》,麥田出版)
世界沒意義也不荒謬,只是存在著
導演蔡明亮說侯麥的《綠光》是影響他最深的電影,原因是「主角在城市中漫無目的地閒晃,好像要尋找豔遇又什麼都沒發生,那種無法融入人群的疏離感,其 實是許多現代人都曾體會的心情」。蔡導也曾在電影中要李康生在街上不斷地走,他的許多電影也少用配樂,而是讓現場音包裹演員的表演。
這讓我想起霍格里耶曾說:「世界沒意義也不荒謬,只是存在著。」而導演的責任就是把這個存在著的世界,透過攝影機重新放映到觀眾的面前。但這並非是寫實主義式的重現,反而是透過刻意的、直覺性的安排,只是高明得不露痕跡罷了。
透過這樣的方式,侯麥探討的愛情、道德、關係、信仰與命運,則像〈冬天的故事〉裡的女主角費麗斯所說的:「突然之間,事情都清楚了。以前我試著去選擇,然後發現根本沒有選擇」般地自然。
多數人的人生建立在微不足道的細節裡,正如許多人的愛情苦於難以克制,自己也都沒有發現妒意,以及各種難以釐清的莫名情緒。這樣的主題並不「輕」,處 理起來更是絕對不輕鬆。侯麥在接受台灣紀錄片導演黃慧鳳的訪談裡,就提到有些想法在他二十歲的時候就有了,卻蘊釀了二十年、四十年才成熟,能夠體現在電影 裡。
在你手上的這本名為《陶瓷碎片》的短篇小說集,就是他在一九四○年到一九五○年間寫就的最初的、未公開的作品,裡頭藏有某些影片最早的靈感。這個書名 據稱源自於他放棄的某篇戲劇劇本的標題,卻恰恰隱喻了這些文字日後在他影像作品裡的意義──即便被打碎了,它們也還是那個名為侯麥電影的美麗陶瓷最初的一 部分。
〈一天〉是《飛行家的妻子》的骨幹,〈求婚〉則是部分的血肉;〈蒙日街〉就是《穆德家一夜》的雛形,〈手槍〉則是「六個道德故事」裡的《蘇珊的生 涯》;〈誰像上帝?〉是《克萊兒之膝》,〈香妲,或試煉〉則是《女收藏家》的部分。〈溫柔的女人〉後來被羅伯.布列松(Robert Bresson)拍成《溫柔的女人》。
「陶瓷碎片」便成了影迷能持有、拼湊電影成形之前,在侯麥腦中停留了漫長時光的珍貴證物。
而愛情是綠光,電影是綠光,小說也是綠光
然而侯麥的電影並非僅有對白,它還有具特色的影像敘事結構,迷人的光影、色彩與演員舉止凝眸的精準掌握。侯麥曾自嘲地說,電影完成他沒有能夠以文字做 到的地方,「如果能做成一個好的小說家,又何必當導演呢?」事實上,侯麥確實在文學事業上遭遇了挫敗,才把心力投注在電影上。
但正如他在一九六五年接受《電影筆記》的訪問時說的:「電影是一種戲劇藝術,但是不應全從劇場上取材,它同樣也是一種文學藝術,不能完全靠劇本和對白來取勝,語言和影像的親密關係創造了一種純粹的電影風格。」
候麥的文學也就是他的電影,而他的電影也就是他的文學。這一點,無論從「道德故事」、「喜劇與諺語」、「四季」系列,以及多部單獨的電影都可以看得出 來。侯麥以鏡頭道出生活裡微不足道的細節,那樣思念、不安、猶豫、謊言、算計、心猿意馬、情感幻滅、解釋與被解釋……。以連綿不斷的對白、微不足道的細節 去建立如斯存在的人生,然後讓角色等待「綠光」的聖靈展現。當微光出現的那一刻,也許你會從沒有配樂的侯麥電影裡,聽到自己平凡人生的最高音也不一定。
侯麥曾說,在他年輕寫這些故事的時候,他並不知道自己會成為一個作家還是導演,我以為這也就成了這批未公開作品值得我們閱讀的理由──影迷們試著從中 按圖索驥,而非影迷則可以看到一個年輕、不服輸又不確定自己才能,想藉說故事表現對世界認識的青年侯麥──那時候那些在影史上不朽的畫面、對白還在他的眼 睛裡,在那雙對人性與愛情充滿激情與好奇,看起來卻平靜如湖水的藍色眼睛裡。
---本文摘自《陶瓷碎片:侯麥短篇小說集》一書,蔚藍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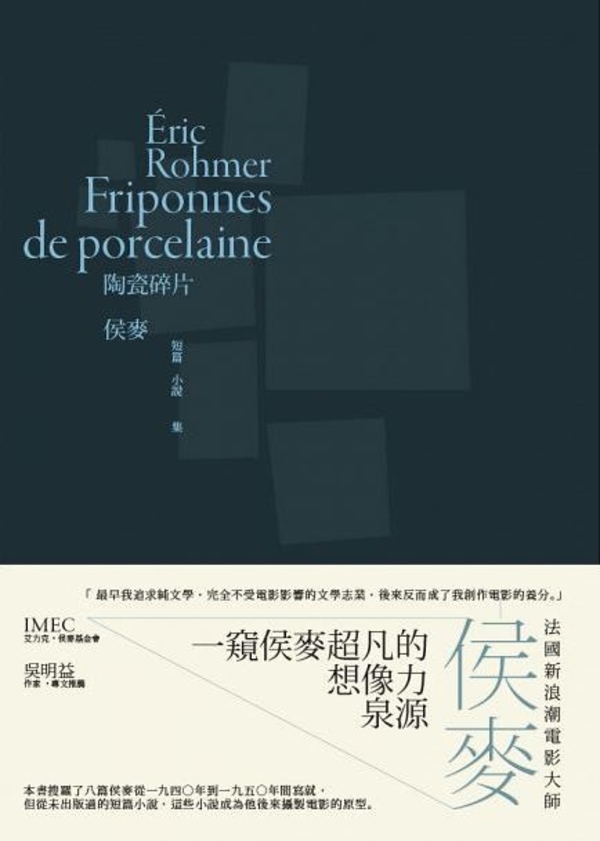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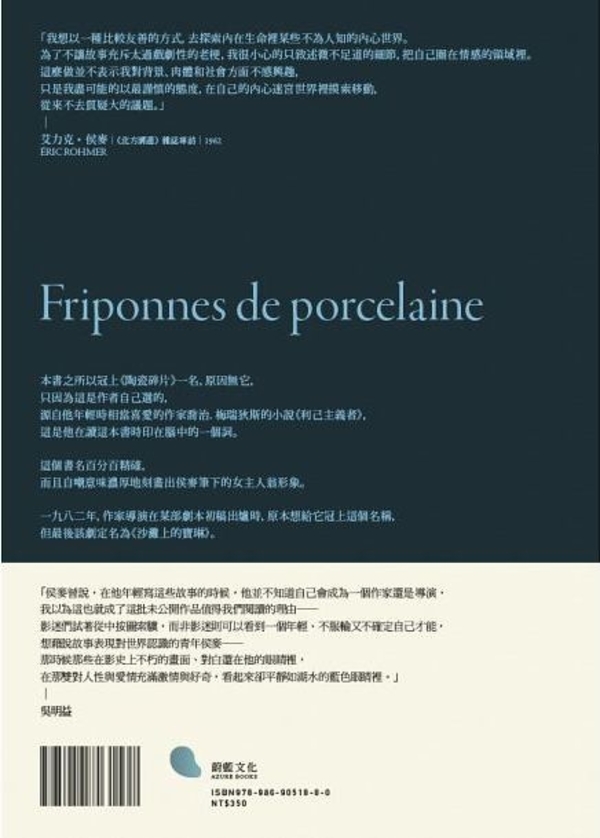 |
「最早我追求純文學,完全不受電影影響的文學志業,
後來反而成了我創作電影的養分。」──侯麥
侯麥最早的夢想是成為作家,而他這些未多加修飾、完全出自他手筆且契合他們那個時代的小說,等於是故事、諺語和喜劇輪替上陣的一部視覺佳作。
本書搜羅了八篇侯麥從一九四○年到一九五○年間寫就,但從未出版過的短篇小說,這些小說成為他後來攝製電影的原型:
〈一天〉是《飛行家的妻子》的骨幹,〈求婚〉則是部分的血肉;〈蒙日街〉就是《穆德家一夜》的雛形,〈手槍〉則是「六個道德故事」裡的《蘇珊的生涯》; 〈誰像上帝?〉是《克萊兒之膝》,〈香妲,或試煉〉則是《女收藏家》的部分。〈溫柔的女人〉後來被羅伯.布列松(Robert Bresson)拍成《溫柔的女人》。
本書之所以冠上《陶瓷碎片》一名,原因無它,只因為這是作者自己選的,源自他年輕時相當喜愛的作家喬治.梅瑞狄斯的小說《利己主義者》,這是他在讀這本書時印在腦中的一個詞。這個書名百分百精確,而且自嘲意味濃厚地刻畫出侯麥筆下的女主人翁形象。
【本文出處。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留言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