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婚(La Demande en mariage)
艾力克.侯麥基金會/〈飛行家的妻子〉檔案,初稿(IMEC RHM 21.2)
一 九四四年夏季完稿於巴黎的這篇短篇小說,於一九四五年春天發表於克來蒙—費璜大學校內雜誌〈船舵〉上。故事描寫一位害羞到幾近病態的男子,羅傑.馬西亞斯 (Roger Mathias),不敢向常在一起的年輕女孩珍妮(Janine)表白。他從旁觀察她,窺伺她,監看她,還趁她去看電影的時候潛入她的住處,整個人可說完 全著魔了。直到某個機緣巧合之下,其實更像是一宗意外的驅使下,兩人在平常閒聊之際,女孩她突然主動向他建議我們結婚吧。
我們也可以把 這篇文章裡長達二十多頁的對白看作在三十五年後才拍攝完成的影片〈飛行家的妻子〉的雛形。文字處處可見探詢式的重複:無意義的對白,人物的懦弱,以及不敢 正面對抗命運而產生的幻想……這裡可以看到年輕作家謝赫的短篇小說中常出現的情境:男主角偷偷跟蹤,企圖搜尋(用視線),擁有他渴望的女人成長路上走過的 每一個地方。不過,本篇描繪的偷窺癖並不帶任何操縱或假意欺騙的意圖。它被定義為純粹的窺探,是不求回報的消極行為。它透露了作家心中那唯有用放大鏡才能 窺伺得的某種偏執:內心的慾望轉換為監視跟蹤等行動。這等強烈的偏執,唯一能表現得出來的情節安排只有靠對白,這已經是侯麥式電影的對白了。
安東.德 貝格及諾爾.艾柏
馬 路還沒開到底;一條蜿蜒小路暫時延續了這條道路,小路兩旁別墅和繁花盛開的院子夾道,遮蓋了底下的鐵路。再往下走,在工人宿舍那排狹窄屋瓦後方,倏忽展開 一片黃橙橙閃著金光的成熟小麥田。單薄的一排排樹,形成圍籬,在麥田縱橫切割,拖著向晚的陽光投射下長長的影子;再遠一點,平原變成統一的灰色,被天光照 得睜不開的眼睛已經看不清那邊村裡的民宅,甚至連三公里外的飛機倉庫的屋頂也看不見了。
「說真的,這裡真不錯。」家路(Gallou)說。「這裡不是很舒服嗎?」
「是啊,遠離塵囂,我們還以為,我不知道啦……」
「是啊,你不會覺得,不會相信我們是在這裡。好安詳,我不知道,這裡這樣的安靜,怪好玩的;我倒想住那兒。」
好一陣子,他們都沒說話。馬西亞斯(Mathias)扔掉手上的香煙頭,用腳踩熄。
「所以,你住那兒啊。」家路說。
他們倆停在一棟茶褐色的別墅前,白色的屋瓦,屋頂非常尖斜。門前石階的上方搭了某種毛玻璃的遮雨板。
「才不是呢!你想得美:那是鄰居戴文納(Thevenet)家。你知道的,賣防水物品的那家店。我得把錶送回去給他們……我住的地方比較遠,在白色房子後面,小路路口那棟。」
「我覺得,」家路說,「這裡真是不錯,很不錯。」一片雲飄過太陽前面,陽光染上一層灰暗的粉紅色暈,映照在四周牆面和樹葉枝頭上。從斜坡上看,已經分不清哪些是樹梢,哪些是蜿蜒的小徑。
家路抬頭望著天空,旋即低下頭。陽光又露臉了。他們沈默了幾秒鐘。
「那麼,明天見。就這麼說定了?」
馬西亞斯伸出手。
「好,就這樣。你今晚要做什麼?」
「我得去給人做掩護。(他看看手錶。)我得到一個秘密情報。」
「啊!是喔。」馬西亞斯說。
家路笑出聲。
「你說『啊!是喔』,那個樣子真好玩。我只是隨便說說,沒有啦!我要去找個傢伙。然後一起去看電影,拉克斯(Lux)影院上映的〈凱西亞〉(Katia)。」
「聽說很好看。」
「對,聽說是。我想是悲劇吧。反正,不是喜劇就是了!據說是不錯。故事發生在俄羅斯,丹妮艾拉.達黎歐(Danielle Darrieux)主演。」
「你認為是在俄羅斯?〈凱西亞〉,我以為是日本的什麼東西呢,凱西亞。」
「錯不了,是在俄羅斯,裡面有丹妮艾拉.達黎歐。」
「真的呢,〈凱西亞〉是俄文。是俄國人名,你說的應該沒錯。我不知道怎麼了,我還以為是殖民地那類的東西。」
「是俄文。這一點,我敢擔保。」家路說。「我看過照片。那麼,再見了。」
「好。」馬西亞斯說。
吉賽兒(Gisele)解不開圍裙的結。門鈴響了兩次。她垂下雙手,跑著去開門。
「啊,是您!不好意思,讓您看見我這副德性。快進來,還有,不要看我。」
她抓起圍裙的一角,沿著對角線對摺,露出圍裙的反面。馬西亞斯走進餐廳;她跟著進來。
「您請坐,請坐。」
她轉身背對著他,放開拉起的圍裙一角。
「您瞧,我下午宰了一隻雞,血噴得到處都是。」
她亮出圍裙布上的斑斑棕色痕跡。笑了。
「我連去找件乾淨的來換的時間都沒有。可是!您坐啊。哎喲!」
「我送錶過來。」馬西亞斯說。
「您人真是太好了,小夥子。看得出來花了很多心力。而且不是德瓦先生(Dewaes)弄的!不,絕不是德瓦先生修的!」
「喔不是的,是我修的。」馬西亞斯說。「幾乎都是我弄的,尤其是比較小的部份。老闆比較沒辦法,因為眼睛的關係。」
「希望如此,希望如此。」吉賽兒反覆說。
她扯掉了圍裙,走過去搬了一張椅子過來,坐下。
「希望如此!」
她望著馬西亞斯。
「您不趕時間吧,您可以喝杯咖啡吧。馬賽爾(Marcel)已經喝過了;他已經去院子了。我們可以不用管他。是不是?」她說。
她走進廚房,順手帶上廚房的門。
從窗戶向外看,可以看見天空已經整個染上一層粉紅。馬西亞斯站起來走到窗戶邊。院子後方,一片草原地勢微微升高,被間隔的相當開的松樹圈住,與一棟比其他宅院更大更古老的宅邸白牆形成對比。吉賽兒回來了。
「您在看天空啊:這裡真是漂亮!您看看這餐櫥的大理石,我這邊。您稍微彎一下腰。對了,剛剛我還以為是黃銅哩。」
她把咖啡壺和咖啡杯放在餐桌上。
「我覺得還不需要開燈,否則就真的浪費了這麼美的光線。我剛剛才跟馬賽爾說呢:您知道的,當我們年紀還小的時候,我們總愛做夢,或計畫什麼的,而且總是夢想著一些小事,是啊。我知道我當時夢想著要有一間房子,有一面窗戶迎著夕陽的房子。」
她笑了。
「是啊,您知道的,我非常在意這一點。我或許是在哪一本書上看到過,總之我非常堅持,非常堅持!好了,現在,我完全得到我想要的了。真是太美妙了,不是嗎?」
她倒好咖啡,走到馬西亞斯對面坐下,背對著窗戶。她面帶笑容;但是馬西亞斯的目光仍怔怔的固定在那兒,彷彿盯著她身後的某樣東西瞧。或許他根本看不清她的五官。
「您不覺得很美好嗎。」,她又問了一次。完完全全是我想要的。我不是說我的腦海裡早就有了一幅像這樣的別墅影像。我看到……是的,我看到的是在對街,上坡的那條街,在對面。我其實並不特別喜歡這棟別墅。是馬賽爾想要。然後,現在,您看看。是啊,現在。」
「一切都十分完美。」馬西亞斯笑著說。
「是啊,現在。」她又說了一次。
他端起咖啡放在嘴邊,沒喝又放回去。光線瞬間消失。吉賽兒起身去開燈。
「好了,換換氣氛;夜幕低垂,總是會帶點悲涼,某些日子裡,真的有些東西感覺非常悲涼。我不知道,如果我孤單單的一個人的話,有些日子我也許會受不了。當我在您這個年紀的時候。」
她揮了一下手。
「我又要說些無聊的蠢事了。您也許趕時間,您今天晚上有事嗎?」
「沒有。」馬西亞斯說,「我會待在家裡。有些時候我會待在店裡。當工作很多的時候。」
「看得出來您很喜歡工作。」吉賽兒說。「您做得對。在您這個年紀。特別是您現在這樣的工作。您比保羅(Paul)大不了幾歲。」
「我已經二十四歲了。」馬西亞斯說,「我都服完兵役了。」
「您已經服完兵役了!您看起來那麼年輕,一定是因為您的神情。當然了。」她繼續說,好像找到一直尋尋覓覓的的東西似的。「像您這樣的年輕人,沒事情做一定不好受。啊,我忘了!您已經訂婚了,是吧。很好,啊,沒有……」
「什麼?」馬西亞斯說。
「不,不,不,不,是我搞混了。」
她看著他,笑出聲來。
「請不要生氣,小夥子……羅傑。沒關係嗎?我可以叫你的名字。可以嗎?好,太好了。我不知道我是怎麼了,我老是搞混,老是出糗。」
「沒什麼大不了的。」馬西亞斯說。「可是您是聽誰說的?」
「是的,我懂。」吉賽兒說。
她再次發笑。
「不,真是太蠢了。」
馬西亞斯一直全神貫注的盯著她。
「是啊,哎,反正跟您說也無妨:您應該不會著惱。我這人只要心裡有一點兒事,就完全擱不住。而且還會胡思亂想一通,真的胡思亂想!對啦,就那一天,我看見您。您跟可愛的賈桂琳走在一起。」
「珍妮嗎?」
「對, 就是這樣。您能怎麼樣呢,我以為──是啦,我就以為您跟我提過,或是哪個人曾經告訴過我──我就以為她是您的未婚妻。就是這樣:我以為是這樣!我這麼認 為,我沒跟您說過。就像一件大家已經知道很久的事,後來就堅定的以為就是這樣了。後來當我又在羅謝家(Rocher)看到她時,我以為這樁婚事已經定了, 就像您親口宣布了一樣;我也不知道,我這!」
馬西亞斯臉上露出了微笑。
「您大概會覺得我有點……」
她揮揮手。
「您能怎麼樣呢,反正又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我不是說她是您的……之類的,您不是這樣的人──不,我們不能這樣說──總之,我是這樣想的。您要再來一杯咖 啡嗎。要,要,要,咖啡冷掉了;我呢,您知道的,冷咖啡我同樣愛喝。加點糖,再一塊。您還真是客氣啊,您。對,我以為是那樣,對啦!」
馬西亞斯拿湯匙在杯裡攪拌。吉賽兒再次拿起咖啡壺,給自己倒了一些,又加了糖。靜寂短短的持續了一秒。他抬起頭:吉賽兒看著餐巾。
「您是在羅謝家認識她的。」他說。
「是的,我注意到她,真是可愛……啊,您對這個有興趣?」她說著瞇起眼睛。
她聳聳肩。
「我跟您說了,就只是個念頭,一個念頭,我並不想……所以,您很驚訝!」
「這個!對,對……就是說……就是您剛剛說的,她是我的……?
「喔,不,也不是特別怎樣啦。相反的,您知道有些念頭啊。反正,這不關我的事。再說,我也許有可能猜對了啊。」吉賽兒笑著往下說。「我想我們怎麼都沒辦法想出個頭緒來的。我就是笨!」
馬西亞斯仍然慢慢的說,彷彿是在對自己說話。
「是的,您會有這樣的念頭還真奇怪,那個……巧合,尤其是……」
「啊,是啊!」吉賽兒盯著他說。
「喔,不,不,甚至算不上有什麼念頭。」
「說說看。」
「喔,不,不行,我無話可說。您會有這樣的念頭其實很自然!總之……」
「說說看嘛。」吉賽兒堅持。
他拿湯匙輕敲餐巾,頭還是不敢抬起來。
「好吧,反正,我可以跟您說……應該要說的……可是……」
「您好像有點煩躁。」吉賽兒說。「您想說,又不想說。您想過,又沒想過。是您?還是她?我都搞不清了,我!您要繼續跟她保持這樣的關係。」
她微微一笑。
「當然,這是您自個兒的事。可是,您這個樣子還真會讓人困惑啊!我不喜歡這樣。」她語帶威嚇的說,同時伸出手指指著他。
「您說的對,這是我自己的事。」他說。「但卻是因為您的緣故。我從來沒想過要開口跟您說。您為什麼要跟我說這些!我從來沒想過您會有這樣的念頭。都是那個巧合。」
他停了一下。
「太蠢了,他接著說,可是我現在卻好想開口跟您說。說真的,畢竟;自己,是的,我……」
「好了,您總知道自己愛不愛她吧。」吉賽兒說。
「是啊,是啊,我當然知道。」
「所以您怕的是她那邊?」
「不是我怕不怕的問題。您能怎麼樣呢,我……我是認識她。可是……是啦,跟其他女孩,可能感覺不一樣。我不知道她是怎麼想的;不對,我很清楚的知道……對,您……其實是因為這事開始的方式。」
「您在您這個年紀就這麼小看自己!我覺得您沒那麼害羞啊!」
「這不是害羞的問題。這,不……其實,您知道,我跟她提過了。」
「啊,然後呢?」
「反正,問題就出在我在提這件事的方式。我跟她說了,又有點像是沒說一樣。」他笑著說。
「真是愈來愈精采了。」吉賽兒說。
她放聲大笑。
「您是愛她,還是不愛她,您跟她說了,還是沒跟她說。您認識她,還是不認識她?」
「我得跟您解釋一下。」馬西亞斯說。「我的確開口對她說了,但是我不知道她是否聽進去了。我確實跟她說了……」
「您到底說了什麼?您說了什麼啊!」
她節奏性的敲打桌沿。好像在質問他的過程當中獲得了無窮的樂趣。
「您確實說了。您知道怎麼說話吧,我想?」
「啊,當然,當然。只是,這話得從頭說起。」
「說啊,說啊,我已經等了半個小時了。現在,我閉上嘴巴。」
「這話要從頭說起。」馬西亞斯說。「對,就是上個星期日。她的梳子不見了(我們之前一起散步)。我們回頭找梳子:是一支紅色的梳子,應該很醒目。剛好路上有個孩子,一個小男孩,我們就問他。」
他看著吉賽兒,臉上露出微笑。
「對,就在那一刻,就在她跟他說話的時候;您知道的,女人比我們更會跟孩子說話。其實,我不太喜歡……」
他揮了一下手。
「尤 其是珍妮……看她跟小孩子說話好像很有趣的樣子:她一下望著我,一下聽那孩子對她說:「沒有,夫人。」我有個預感,覺得好像她是因為孩子說了這句話才抬頭 看我,但是我不敢確定,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真的有點太蠢了!因為一個小孩子說了一聲「夫人」,或「小姐」,就這樣,他隨便跟任何人都可能這麼說,總 之……,他沒看到任何東西。她跟他道了再見,然後他回答:「先生,再見;夫人,再見。」沒錯,就是這句話逗得她笑了,沒別的!您知道她是什麼樣的人。
不,您對她的認識不深:她笑著說:『他稱呼我夫人吔!他叫我夫人!』她說這話的時候,一副傻大姊的模樣,對,真的是一副傻樣兒。我呢,我也笑了,然後我就 說:『您想怎麼樣呢,他以為您是我的妻子……這些孩子們……──啊,他以為我是您的妻子!』她笑得更厲害了。『所以,這話您聽了覺得好笑』我對她這麼說; 我拉住她的手臂:『您聽了這話想笑,您覺得這話很好笑!』然後她就走了。」
「她走了……」吉賽兒說。
「對,我們在路上,在林道變成馬路的連接處。我們離開小男孩的時候才剛走出林子,我們穿過馬路,然後穿過草原,想這樣切過去比較近。她走得又急又快,剛開始我還以為她會跌倒;後來我看出她不想回我的話。我邊叫邊跑過去:『對,我的妻子,我的妻子。』很蠢吧,您不覺得嗎?」
「後來呢?」吉賽兒問。
「後來!沒啦。我不知道她到底聽見了沒有。當我們走到大馬路上時,有人看見我們走下來。我繼續走著,一路上都聊些別的事。我甚至拍了她的照片。我們出門時。一開始她還不願意;她說小幅的照片她都照得不好看,還說她會吐舌頭。可是當我開口要求時……」
「她吐了舌頭?」
「沒有。她擺出那副表情,沒錯,一副很棒的表情。」
他掏出皮夾。
「您看得出來嗎?」
「對,她這個樣子好親切。」吉賽兒說著拿起相片。「希望如此。希望如此。您拿相片給她看了嗎?」
「看了,照片洗出來之後,我就拿給她看了,那天是星期三,就是前天,但我拿的不是這一張,是另外洗得比較差的。她說她人看起來好黑。於是我就說我拿去重洗。我今天早上有看到她,只是當時我還沒拿到相片。」
「所以,現在呢?」
「現在,現在……」
他高舉雙手。
「我不知道……」
「您還是可以問她嘛,不是嗎?」吉賽兒說。「但這得由您決定。您想怎麼樣呢?」
「我同意您的看法。」他說。
「您看您讓我說出什麼話來了,什麼話啊。說真的,您問我對這件事的看法,還真是不尋常:我必須說。這又不是我的事。」
「喔,這點我很清楚。」
他的眼睛一直望著餐桌,固執地。
「總之,如果我理解的沒有錯……您允許我整理概述一下嗎?您敘述的方式真特別……您和她出去,她弄丟了一件我不知道什麼的小東西,梳子。您找到一個小孩子,問他有沒有看到。他稱呼您們「先生」和「夫人」。這話讓她發笑,所以您決定放膽一搏。」
「完全不對。」馬西亞斯說。「我說的是:『有什麼東西那麼好笑?』的確是沒有什麼好笑的啊!我是看到她這麼傻傻的笑:一個孩子有可能會弄錯。」
「好,好,我道歉。」吉賽兒說。「您真是難搞,我可憐的羅傑。所以您說這些話,完全沒有弦外之音;我這樣說對嗎?」
「對,完全沒有弦外之音,對,至少在那當下沒有。」
吉賽兒笑得更厲害了。
「是之後,您才有了非份之想,您真的要笑死我了。總而言之,所以是她聽出來了。」
「喔,不,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聽出來了。」
「聽我說,我們再回想一下:我又沒跟上了。如果您什麼都沒說,她也什麼都沒聽出來,我完全看不出……」
「沒聽出來?沒聽出來。我不知道?是,我是有點誇張,您想怎樣呢!您知道的,在敘述的時候……對,您說得有道理。事實上,當我大喊那句話時,我是想看著她講,但我們彼此並不是面對面。」
「所以?」
「對,她跑走了。」
「然後呢,您有繼續喊嗎?」
「沒有,我哼都沒哼一聲。」
「就這樣結束了。」吉賽兒說。「您快把我搞瘋了。」
「您說得對。」馬西亞斯說,「我真不該跟您說這些。可是……」
「是啊,總括來說,您等於什麼都沒說。」
「對……是啊,總括來說,我是等於什麼都沒說。」他盯著吉賽兒,重複她的話。
她收回放在桌上的手肘,身體微微往前傾。
「您想怎樣呢,如果您在害怕!怕……」
「當然不是。」馬西亞斯突然說,「說出來其實不難。這一點,一點都不難。更何況,我有的是時間。這不難。難是難在之後。唉,我又跟您說蠢話了。您說的對,我是個大笨蛋。」
「所以,您怕的是答案囉。」吉賽兒以相同的質問口吻說。
「答案?她想怎麼回答就怎麼回答,應該說問題出在我身上。」
他露岀一絲笑容。
「您說的對,我是個不折不扣的大笨蛋。」
「總不會是您愛她的這個事實讓您心生恐懼吧?」
「怕愛她?害怕什麼?您說的有道理,這真是蠢透了。」
「您懂我的意思吧。」吉賽兒說。
「是,是的,我懂。我只是在想我幹嘛跟您提這些。為什麼會把這件事說出來。為什麼?」
「總之。」吉賽兒說。
她話沒說完便打住。她聽見馬賽爾上樓的腳步聲。他們暫不作聲,直到門打開。
---本文摘自《陶瓷碎片:侯麥短篇小說集》一書,蔚藍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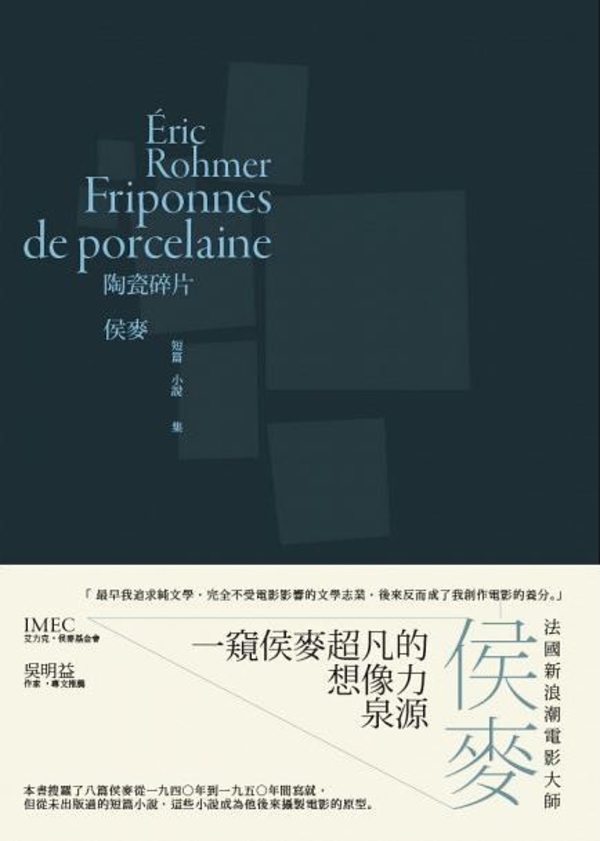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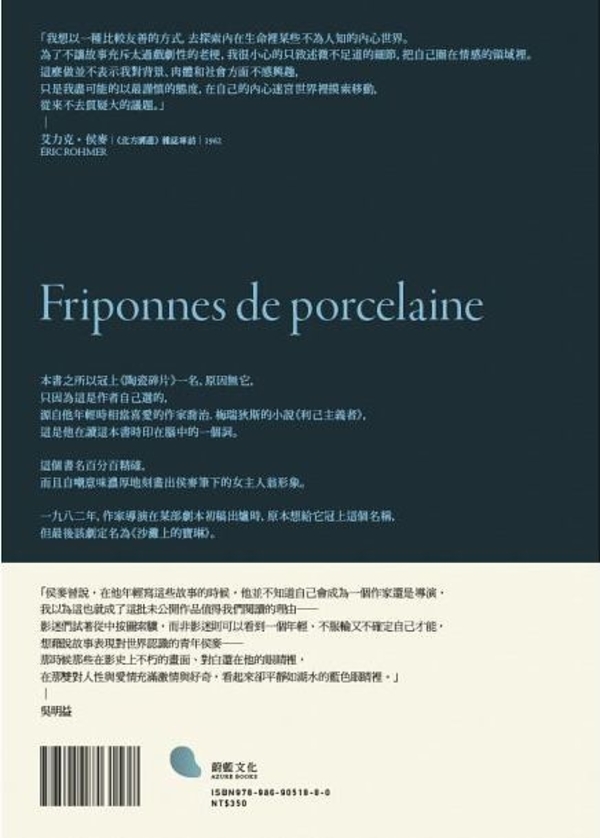 |
「最早我追求純文學,完全不受電影影響的文學志業,
後來反而成了我創作電影的養分。」──侯麥
侯麥最早的夢想是成為作家,而他這些未多加修飾、完全出自他手筆且契合他們那個時代的小說,等於是故事、諺語和喜劇輪替上陣的一部視覺佳作。
本書搜羅了八篇侯麥從一九四○年到一九五○年間寫就,但從未出版過的短篇小說,這些小說成為他後來攝製電影的原型:
〈一天〉是《飛行家的妻子》的骨幹,〈求婚〉則是部分的血肉;〈蒙日街〉就是《穆德家一夜》的雛形,〈手槍〉則是「六個道德故事」裡的《蘇珊的生涯》; 〈誰像上帝?〉是《克萊兒之膝》,〈香妲,或試煉〉則是《女收藏家》的部分。〈溫柔的女人〉後來被羅伯.布列松(Robert Bresson)拍成《溫柔的女人》。
本書之所以冠上《陶瓷碎片》一名,原因無它,只因為這是作者自己選的,源自他年輕時相當喜愛的作家喬治.梅瑞狄斯的小說《利己主義者》,這是他在讀這本書時印在腦中的一個詞。這個書名百分百精確,而且自嘲意味濃厚地刻畫出侯麥筆下的女主人翁形象。
【本文出處。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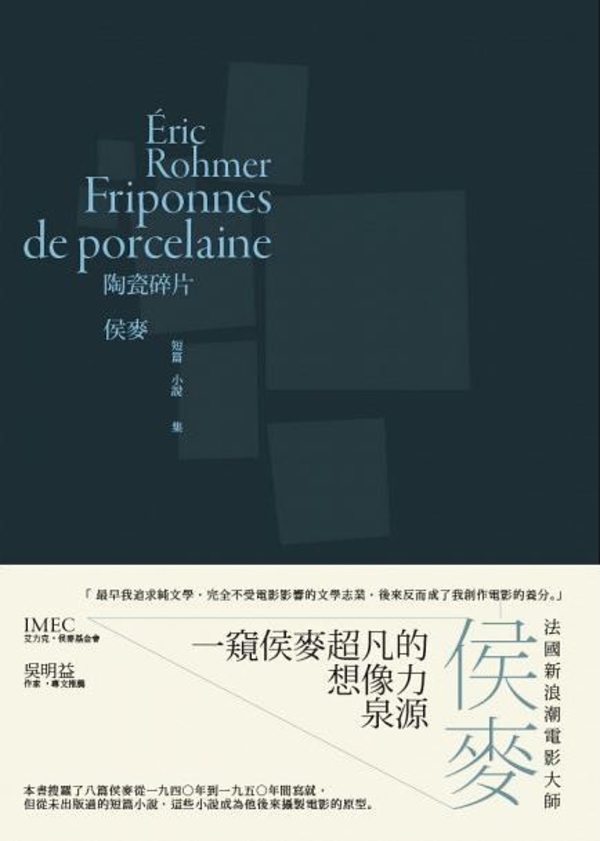










留言評論